我所记录,只是我所到过的一座城市位于郊区的农业社会的部分,现在,它被扩展为城市。
——题记
桃花岛从前一年叫果园,从前十年叫柳树湾。
它逶迤着,一半靠着淮安城,一半贴着古黄河的边。
岛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也许是几百户人家。他们大多数以种果树为生,还有一些人,不仅种果树,还养奶牛,所以,又有人管这一带叫奶牛场;而另有一些人,种了果树,养了牛,又把门前的一个大水塘挖深了,从古黄河里引过水来,在里面养鱼。先前只是养朝鱼,也就是鲫鱼。后来又买了一些鳊鱼、大头鲢子的幼苗。于是,这池塘里的鱼就既有鲫鱼,又有鳊鱼和大头鲢子了。去年,还出过螃蟹和两只饭碗大的甲鱼。
有一天,下大雨,水漫过了谢小六子家的池塘,鱼们都跑出了池塘,谢小六子一家只好全部出动来逮鱼。
他们的小二子,才十岁,背着书包,正要上学去,也被谢小六子叫了回来。帮着大人捉鱼。
不少鱼还没长大,还要再长一长,才可以吃,如果去卖,那更不行,这些鱼大多还只是鱼秧子,太小,若卖了,恐怕还不够鱼苗钱。
所以,所有跑出塘的鱼都要统统逮回去。
他们拿了脸盆,拿了水桶,连水带鱼往池塘里舀。在谢小六子的心里,天下的东西,鱼最娇贵,性情也烈,沾不得人气,你若用手直接抓它,即使把它放到金水银水里,它也好说歹说地不长了,甚至过不了几天,有的就要死掉。
水漫得太多了,谢小六子的女人负责用泥围坝堵鱼,她堵了左边塘口的鱼,右边的泥坝又被水冲坏了,那放水引流的,是她的大伯子谢小五,他还没睡醒,就被他的兄弟喊来了,裤角也没来得及挽,就下水了,他一边放着水,一边堵着鱼。忙得一头汗,忽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他就成了个泥大伯子了。雨停了,看热闹的人多了起来,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牵着一头牛,也来看热闹,他拍着牛,故意弯了腰说:捉鱼喽,谁捉到就算谁的。
又一个人接着道:你要捉,别捉朝鱼,你单逮那大头鲢子,鲢鱼头烧豆腐,鱼尾红烧。
他们这样大声说着,笑着,做着捉鱼的姿势。但并不行动,好像专等谢小六子来请他们似的。
那谢小六子向来是个豪爽的人,他说,不就两条鱼嘛,算什么大事,一会儿给你个三五条。现在,你们倒是帮我呀。
于是,那看热闹的便纷纷地脱了鞋,帮着他们捉鱼。
放掉了多余的水,留住了鱼,修好了鱼塘,天已经中午了。谢小六子从塘里网了两三条大头鲢子,又网了半桶半尺来长的小朝鱼上来,吩咐他的女人:去,买个十瓶八瓶酒来,都到我家吃饭去。
他的女人去买酒,没买十瓶,也没买八瓶,她算了算,一共十几个人,酒量最好的是李二爹,他喝足了也不过一斤,堂室摆一桌,院里摆一桌,再加上自己家的人,有六瓶酒总够了,家里人还可以少喝点。
谢小六子的女人擅烧鱼,煮汤。不一会儿,菜做好了,上了桌,大家都夸这鱼塘养的鱼就是比街上买的鱼味道美,一个人说:明年我也想法子弄几条鱼养养。
另一个说:吃买的鱼总觉得不够味。
因着这么美的鱼,六瓶酒一会就喝尽了,谢小六子又打发他的女人去买酒。这女人狠了狠心,心想这次一定要买够,否则会让人笑话她小气的。
即使买多了,喝不掉,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下次总还有有事的时候,留着下次再用好了。如果她的男人馋酒,要自己喝,那却不行,她要把喝剩的酒想法子藏起来,他是不去厨房的,就藏在厨房碗橱的大抽屉里,他若问上次请人捉鱼剩的酒呢,她就故意生气地说:还不是全叫你们这些小和尚给喝光了。
她买的是分金亭酒,四块钱一瓶,还有两三块钱的,但买那种酒,她的男人一定是要怪她的,再说,乡里乡亲,也不好看。所以,她又买了六瓶分金亭。
这一个小鱼塘一年下来,能挣多少钱呢?除了鱼苗、鱼食,多打多算也就千八百块吧。
这一顿饭,要不要算进成本呢?当然不能,即使天不下雨,鱼不跑,弟兄们,邻里们也总是要在一起吃个饭的。
人活一辈子,图个什么呢?还不就图个热闹,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把时间给打发了。
她再不济,这个道理总是懂的,所以,她不仅又买了六瓶酒,又顺带买了半只酱好的猪头,二斤水煮花生。
而那当时四块钱一瓶的酒,现在已经不出了。有的人家颇有收藏,隔了这十年后拿出来,又香又清冽,像是很淡,抿一口,竟比茅台甘甜有味,比五粮液味思美思醇厚。它仿佛在时间的水里祛除了一切人间的火气,瓶子竟也是那样的普通而且有生来的旧,像千年的仙子终归耕于尘世,素服布衣,做着人间平凡新妇的事情。
果园的人,给小孩子起名字往往是顺手拈来,仿佛在小孩子的名字上动脑筋,是世上最大的关于时间的浪费。
三四十年以前的夫妇生小孩子,全凭天意,孩子总是来得多,来得也快,一不留神,生上三五个,是很平常的事。
小孩子一个跟一个地出世,总是来不及起名字,何况不出世,也不知道是男是女,所以,只等生出来再定。
名字总是来得及起的。如果刚巧东家才生了一个公子,这公子姓张,起名为建华,建设中华之义,西面这一家呢,觉得这名字起得真是好,碰巧没过几天,他家也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家姓朱,就顺着东家的法子,叫朱建华好了。
心思缜密的父母,也有不照搬照用的,往往改动一下,若看好了力字,那就把建改为力,叫力华,若是看好了建字,那就改华字,改成什么呢?一抬头,门前全是长得青青葱葱的苹果树,就叫建树好了,或者跟着自己家的班辈用字定,如是玉字班,则叫玉树,如是文字班,则为文树。
另一个人家,他家碰巧有一台收音机,此间正在播出评书连播《水浒传》,正讲到燕青卖线,他觉得燕青这名字起得实在是好,燕子一来树发青,心下便想好,如果三两年的,也生那么一个男小孩,不叫别的,也叫燕青。可过了一年多,他只生下一个女小孩,那也没什么关系,还叫燕青,总比浪费了不叫可惜。是不是过上一两年的,总还能生到一个男小孩,一是这名字太好,千年难遇,只有快用了才心安,其次是怕过上个三两年的,就过忘记了。
至于这女小孩,叫西施岂不是更好?西施在此地本是家喻户晓,但西施据说是杭州人氏,离得太近,显不出为父的经多见广的精神,再说,人人都知道出处,未免就显得土,另也就失去这一番良苦用心的意义了。
总之,孩子一出世,那做父母的灵感也就油然而生,如有神助似的,一张口,名字就起出来了。
讲究的人还能一下子想出两三个,进行权衡,比较,这两三个待用名,若都觉得好,不妨先用一个,另一个留着下次用,但这次用哪个好呢,那就问问别人,让别人帮着拿主意好了。
杨现定今年怕有四十多岁了,他的父亲是渔民,天天在里运河上弄船,杨现定没生之前,那怀孕的女人问那整天在河上的男人:
这毛毛叫什么,省得到时你不在家,我不知道叫什么好。
毛毛,就是刚生下的还没名号的小孩,可以一律叫毛毛,狗狗,丫丫,蛋蛋,也可以叫宝宝。
淮阴人猫字总是咬不清,要读成扬声的毛字,所以,养猫听起来是养毛。而那毛毛,也许是毛毛,也许只是家中的小猫。
这摇船的男人吸着旱烟,想了又想,没想出个子丑寅卯来,过了半天,极珍惜地说了两个字:
现定。
这女人生孩子时男人果然没在家,户口总要报,这女人想了又想,记起来了,他的男人是给娃儿起过名字的,娃儿是男的,就叫杨现定。
杨现定的女人叫陈梅之,至于到底是梅之还是梅子,仿佛杨现定也是弄不清的。
这女人是杨庄人氏,顺着大运河走下去,过了杨庄大闸就是,离果园至多三四十里的路程。
杨现定年轻时也跟着父亲在船上,后来船出了事,船没了,整个家当也就没了。
杨现定只好买了两头小牛养。果园的草好,小牛养活了,养大了,卖了钱,他又买了两头小牛,买了七八只小羊。
女人在家。她不喜欢牛,也不喜欢羊,她买了两只小猪,春天和夏天,天天提着篮子割猪草,喂猪。
入了冬,那小猪变作大胖猪了,杀了一只过年,另一只是母的,留着来年生小猪。
杨现定和所有的男人一样,一高兴便喜欢喝点酒。也喜欢骂女人,他不骂东家的女人,也不骂西家的女人,只骂他自己的女人。
她喂猪迟了,他骂,不迟呢,也骂上两三句。
喂迟了,他说:
你是诚心耽搁我那母猪长肉。
不迟呢,他说:
你这女人,把猪当男人养,生怕喂迟了,饿死它。
天下有没有没脾气的男人?恐怕没有,男人天生要骂女人,女人天生要挨他们的骂。
这样一想,觉得骂也就骂了,也不疼,也不痒,他骂了人,他也没比别人多长五两肉。
至于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她哪里不小心招惹了他,让杨现定自己说,恐怕也是说不上来,可是,在他眼里,她仿佛是没做过一件对事似的。
是她说错了什么吗?她仿佛不太爱说话,她也懒得理会他。
他有时也不骂她,一连几天,他哼着淮剧,哼了《赵五娘》,又哼《打金枝》还有《十不孝》:
娘怀儿一个月,不知不觉,娘怀儿两个月,呕吐恶心。
他对他的女人说,我对你是好的,女人不骂不成器。
又说:我舍得骂猪,舍得骂狗,也舍不得骂你。
可他若真的又骂了她呢,骂也是白骂。
天下的法律,有管男人骂自己女人的吗?
恐怕没有,他也从没想过,不单他没想过,他的女人也没想过。
哪个女人,一辈子不遭自己男人骂呢?
男人活一辈子,忙忙碌碌的图个啥,无非是图个顺当,图个清静。男人找女人干什么呢?随时由着自己出气吧。
兼之在一起吃饭,睡觉,生小孩子。
夫妇之道,不过如此。
年轻些的时候,这女人挨了骂,也是会生气的,生了气怎么办,她不会骑脚踏车,也舍不得坐汽车,她一气之下,走了三十里地,走回了娘家。
若她的气生得不太大,她在娘家住上两三天,就自己回来了。
若气到极处,想了再想,还想不开,她便发誓不回家了。
有一次,她果真生气气得厉害了,于是,在娘家一住住了六七天。
话说那杨现定,心里也是拿定了主意的,他对他的嫂子说:
看吧,住不上三两天,她保准自己回来。
回娘家这一招,杨现定早有领教。按惯例,她若回去想一想,不生气了,住上两三天,她自己就回来了。
若想一想,还生着气,她自己多半是不会主动回来的,她要等着他亲自来接她。
这一次,她狠下了心,想着,即使他来接,也不回去了。杨现定那面呢,一看几天还不回来,也有了数,自知这一趟路是少不了走了,只好又硬着头皮去接她。
除了过年,端午,八月十五,他是很少去他岳父家的。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接闺女回门,他也是不去的,她女人同着小孩子回去,买不买东西,无所谓,他若一起去呢,他是要面子的,总要带上几色礼,所以,为了省钱之故,他能免去则免去了。
现在,他去接他的媳妇。他打了两瓶酒给他的岳父,又专门去著名的西园糕点店买了两包桃酥给岳母,小姨子嘴巴坏,不好应付,他只好花五块钱买了一块据说是纯羊毛的红围巾给她。
杨现定提了酒,桃酥,怀里藏着红头巾,又带上七岁的儿子。
他早想好了,一见面先赔不是,草稿业已经打好,他要郑重其事地对她说,不要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左右跟我回家去吧。当然,这话不能虎着脸说,要笑眯眯的,他不由自主笑了,算预习。
可一进他岳父家的院子,他的男子汉的威风又扬起来了,他想好的话,好像全忘了,都派不上用场了。
他见过岳父母,见过小姨子,才去西屋见他的女人,他的脾气又来了,好像他不是赔不是蜜风果园,而是兴师问罪来了。他说,你这狠心的女人,只顾自己过上了太平日子,猪也不管了,羊也不管了。
实际上呢,杨现定这五六天,猪管得好好的蜜风果园,羊也管得好好的,孩子也管得好好的。倒是他自己,因为又管猪又管羊,还管着一个七岁的小孩子,一天忙得连饭都省下了,来不及吃。
杨现定来了,也没赔礼,也没道歉,这女人呢,也一转眼忘了自己当初发下的永不回家的誓言。她连饭都没有吃,便一言不发地跟着杨现定回家去了。
过了几天好日子,杨现定嘴里的脏话又飘上来了,他骂了猪,骂了羊,骂她,骂她把鸡喂瘦了,骂她把猪当男人养。她呢,也安心地受着,日子嘛,也照样过下去。
果园的男人、女人,好打抱不平。
好打抱不平的女人对杨现定的女人说:
下次他再骂,你索性回去住上一年。
如果她知道杨现定的女人在淮安的某个偏远小镇有远房亲戚,这亲戚平时素少来往,杨现定是没见过面的,她就出主意说,你就住到那儿去,让他找不着。
好打抱不平的男人对杨现定的女人说:
杨现定再欺负你,到我家睡觉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杨现定还是张口就骂他女人,而他的女人呢,既不曾藏到她的远亲家去,也没去别的男人家睡觉。
他们盖了三间漂亮的大瓦房,儿子上了技校,最鼎盛的时候,养过三头猪,五头牛,三十六只羊。
桃花岛民风古朴,物华天宝,小闺女们,个个生得干净、漂亮。
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个漂亮的外村的闺女往果园里嫁,而不见一个果园的闺女嫁到外边去。
杨树德的五闺女杨青荷,小名五儿。这闺女本是该生在八月的,可六月还没了就出世了,苹果还是青的,而荷花正好开,就临时起了青荷的名字。她的大姐叫冬梅,冬天生的,二姐呢,九月生,叫二菊,三姐的名字曾是担负着重任的,叫招娣。可叫了招娣,也没招到小弟弟。他们又生了个闺女,这闺女生了出来,杨树德也没完全绝望,只觉得是招娣这名字没起好,于是,将这四姑娘的名字命为唤弟。这杨小五还在他女人肚子里时,他便将那五娃娃的名字取好了,他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无论这次生男生女他都决计不再生了。他怀着必胜的信心,但也有再次败阵的思想准备,所以,他给那没出世的预计将在八月降临的小娃准备了两个名字;男孩儿呢,因为是园字辈,叫园贵,女孩儿呢,也叫什么桂好了,反正是表示桂花开了的时候所生的意思。
可他终究没生到园贵,连桂花的桂也不来了,只来了青荷。
这杨树德虽说是生女气短,但爱女一样情长。
他如此一鼓作气地生了五个女儿,也是可以在果园的历史上记下辉煌一笔的。
前四个闺女暂且不表,单说这五姑娘。
五姑娘据她父母的理论是早生了一个多月,可她一生下来便明眸,乌发,圆脸,小嘴,健康,活泼,结实。
被杨树德所约,来见这奶娃娃的朱奶奶说:肯定是足月所生,肯定是当父母的这两个人生性糊涂,所记有错。
朱奶奶年将七十,夫妇和睦,高堂犹在,儿女双全,所谓五角俱全之福人。
婴儿满月,抱出来,人人看了头,又看脚,皆说:至少有十年果园不曾有过这么有样子的小东西。
对此,杨树德一百个确信,恨不得真的买个蜜罐子,把五儿捉进罐子里去养。
那时,岛上的女人多是到古黄河里漂洗衣裳,如果是冬天,就中午去,若是夏天呢,多半是晚饭后,她们用盆端着脏衣服,衣服里裹着“大运河”牌肥皂。
这大运河牌的肥皂可是家喻户晓,因为是本地产品,价格实在,品质呢,仿佛再没有一个牌子比它更让人放心了,这果园朱家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大运河牌制皂厂上班,那三个孩子,都是大家看着长大的,厚道,诚实,这样的孩子所在的工厂也一定不差。
至于所买的肥皂是不是那三个孩子亲手生产的,他们并不计较。
杨树德家用的也是大运河牌肥皂,他们喜欢这个名字,大运河是他们从小长大的地方,那有码头,有船,有他们的童年。杨树德二十岁时就吸烟,以前买不起成包卖的,要自己种烟叶子,再将其搓碎,所谓吸烟就是用纸卷那烟叶末子。而成包的金贵且好,所以要称之为香烟。那时卖香烟也并不是都成包卖,而是拆开了,论根卖,一到了春秋天,口袋里有了钱,杨树德便隔三岔五地买上一根现成的香烟吸,烟品种很多,有“大生产”牌的,有“华新”牌的,有“大运河”牌的,他买烟只买大运河或大生产牌的,这些牌子让他放心、踏实,味道好,价格公道,杨树德年轻时理想的生活就是一天花上一毛五分钱买一包大运河牌香烟。当然,若再搭上二两散装洋河,四两猪肉,帝王的日子亦不过如此吧。
杨树德的女人洗衣服,那队伍是蔚为壮观的,她在前面走,后面一路跟着几个小姑娘,抱洗衣板的抱洗衣板,拎盆子的拎盆子,拿肥皂的拿肥皂。那上了学的大女孩,还把她的作业本带上了。五儿最小,小虫子似的,总是一步不离她的母亲。仿佛她不到场,她母亲的那些活就无法开工,她跟着她妈去洗衣裳,先是用手牵着她妈的衣服自己走,可走着走着,她不想走了,她张开两只小手,让她妈抱。
卖果子的时节到了,这是杨树德最高兴的日子,他种的果子大,而且总比别人家的能早熟两天,别小看这两天,这两天不只金银不换,也是杨树德在果园最有威望的时候,这两天的果子若是金果,他杨树德卖了两毛钱一斤,再过两天,别人的果子上市,就只是铁果铜果了,只能卖一毛五六一斤了。
所以,他是高兴的,他一高兴,就买了一根香烟,二两酒,那猪头肉,他想了想,一狠心,称了一斤。
杨树德嘴里哼着淮剧,把烟夹到耳朵上,把酒提在手里,猪头肉藏在怀中,回到了家。
她女人洗衣服去了。他追到河边,他的女人正在水里拧衣服,冬梅、二菊爬到一棵桑树上摘桑果,五儿和她的四姐唤弟爬不上去,五儿在呜呜哭,唤弟则使劲往树上扔石子打她两个姐姐,招娣则不声不响地一个人玩草叶。
杨树德呢,他既没叫冬梅、二菊下来,也没管唤弟和招娣,他一把抱过五儿,把五儿抱回家,和他一起吃猪头肉去了。
吃到高兴处,他点着了那支大运河烟,又用筷子蘸了一点酒,让五儿去尝,酒辣,五儿大哭,五儿一哭,他笑得更响亮了。
偷着给五儿吃猪头肉,有案可查的。大姐冬梅说是两次,二菊小,眼不精,所以她说是一次,三姐招娣最是会糊的,历来天地不怕,她说,五次之多都是少算,而四姐唤弟虽只比小五大那么一两岁,但待遇完全不同,所以她每逢遇此,都一言不发,说了也是白说。
除猪头肉,还有杨梅,淮安不产杨梅,可五儿看到了,要吃,杨树德就买了一大捧给她尝鲜。夏天的西瓜,一人一块,可一比,总是五儿那块大些。
四个姐姐不服气,总是找她们的母亲评理,杨树德也不服气,他用手指点了冬梅、二菊,又点了招娣和唤弟,说:
你,还有你,你们这几条馋虫,哪个不是在你妈肚里不挨风不淋雨地待了九个月,你们小妹,不折不扣你们一奶同胞的,她只待了七个月,这少待的俩月,一百头猪也补不回。
转眼五儿就长到了二十岁。
五儿高中毕业了。大姐在纱厂工作,二姐读了技校,但二姐也在纱厂上班,招娣最争气,读了大学,毕业后就在南京不回来了,唤弟呢,她只比五儿大那么一两岁,但已经要结婚了,果园的人喜欢将小姑娘的待嫁之夫呼之为小和尚,这位小和尚没什么工作,他的父亲开着一个豆腐房,做了一辈子豆腐,他的母亲卖了一辈子豆腐,他们只生了这一个儿子,十七八岁时送到城南一个汽车修理厂去当学徒,可他嫌那活儿脏,跑回来了,跑回来干什么呢?只好传他父亲的手艺,做豆腐。
一个壮实如牛的小伙子做豆腐,杨树德实在想不通,但都是果园的人,三媒六证的,实在难以发表不同意的心声。再想想自己,不过也是养养桃树而已,因此也气短,人家不就娶你一个闺女吗?你又不是仅此一个。如此一想,也就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了。
但他也许确实有些老了,从此他便不大出门了。
果园里果树成熟的季节,家有果树的都在果园里搭棚子,二十四小时看护果树,棚子要搭得比房子高,吃饭在里面,睡觉也在里面,站在棚子里四处一嘹望,每棵树都一目了然,哪棵树的桃子见红了,哪一晌风大了,风吹落哪棵树的果子了,谁伸手摘一只桃子了,都看得一清二楚。这看果树的,多是年轻的小伙子,有一阵子,唤弟的小和尚也被人请去看果树,唤弟也去了,晚上也住在棚子里,不回来睡了。
唤弟一说话也是会让人生气的,比如她说:
没什么营生比做豆腐更好的了,一辈子吃豆腐不愁。
又比如,她说:
美中不足,只是这豆腐房开在果园,最好开在百里之外。
杨树德一向是喜欢吃豆腐的,果园里会做豆腐的不下五六家之多,偏偏他就认为这一家的豆腐好,不老不嫩,味道正。
所以他从此不大想吃这一家的豆腐了。
他有一次,骑车去市里的菜场,专门为了买豆腐,他一口气跑去,买了来,又觉得那味道实在是不那么好。吃惯了一个人做的东西,再去尝别人做的,实是不易之事。
果园里对于大了的女孩,是呼为小大姐的,而对于大的结过婚的女孩则呼为大小姐。
杨树德家的大小姐二小姐,一个嫁给大卡司机,一个嫁给石化厂的电工,都是根正苗红,至于三小姐,早些时听说已有主,只是至今不曾见过,想来也是不凡的。
现在,五儿长大了,蘸着果园的露水,吃着母亲在果树空地和黄河边上见缝插针种下的五谷杂粮,日益生得眼睛亮,头发黑,结实、白净。
果园的人提到杨树德几个闺女,往往不大叫名字,而是呼为大小姐二小姐,或三小姐四小姐的这么叫着,这最小的一个,他们却不叫她五小姐,可能是因她尚未成年,也不-1她青荷,而只叫五儿或杨家小五。
她学习成绩不大好,但也读完了高中,也算是读了十几年的书了。
果园里的姑娘,出路不多,读不上大学,多半是去牛奶场,挤牛奶,刷奶瓶子,如果城里征用土地,那就等着被招工。
招工的工种总是不大有好的,唯一的好处是把户口变了,果园的人多半是农业户口,一招工呢,就变成城市户口了。那城市户口又有何意义呢,据说是好,至于如何的好,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清。
五儿曾经也想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去纱厂,但杨树德说什么不舍得,纱厂太累了,五儿一向娇弱,好姑娘也累成坏姑娘了。
因此便罢。
五儿二十岁了,桃花岛的风俗是要办酒席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女孩子们在娘家过的最后一个整生日,以后到了婆家,吃苦受累,都是她们的命了,她们再也受不到那么多父母亲的疼了。
过生日总是隆重的,果园的女孩子一过了这个生日,可就是正式的大人了。
这么娇贵的手掌心里养大的女孩儿,真是不忍心送到别人家去。
有时,她帮母亲理菜,母亲不用她,说:
干活的日子有的是,不必在今天。
五儿帮爸爸去弄果树,还没到跟前,她爸爸就看到她了,他说:
你去,这不是大小姐碰的事情。
那一年,城里的新亚商城开张,招营业员,五儿的条件,样样够,但因为中间没找到得力的能说得上话的人帮忙,也只好放下不表。
我要离开桃花岛的时候,才认识五儿,后来她嫁给谁了?谁做的媒?她有着怎样的一个前程?李家奶奶说起来是一个版本,东家的姨娘和五儿是亲戚,她说起来又是一个版本,而陈家因为一直妒忌着杨树德养果树的水平,所以陈家女人说起来,便又是一个版本。
这么多年过去了,冥冥中的定数是否一一君临?
五儿是不是仍然那么爱美?仍旧一见之下便眯眯地笑,温柔地同人打着招呼?在时间之水中,她好像是什么难处也经历不到,只是一个在掌心长大的种果树人家的姑娘。
四
果园的最西边住着杨四爹。
在北方,爹是父亲之意,在果园,杨四爹是杨四爷的意思,比如,一个果园的小孩他喊爷爷,他是不这么喊的,他喊爹爹。大爷是大爹,二爷是二爹,小爷则是老爹。
小孩子上了学,学了普通话,知道了礼义尊卑,知道城里的外乡的人是将父亲的父亲呼为爷爷的,可是知道如此,也只作心里的明白,他还要喊那上年纪的为爹爹的,至于为着什么?只不过是历来如此罢了,也怕喊了爷爷,而那做爷爷的却不知道应承。
杨四爹住在果园最西,人们当面是这么恭敬呼唤,背后却喊他西大边杨四。
为着什么,也许只不过为着他是一个后来果园扎根的外乡人吧。
至于外乡,倒未必有多么远,洪泽湖的乡下,离此也不过七八十里吧,那时的路程,既无法以车时计,亦不知看看路上是否有标识,一个小时走上十里地,走上一天,也不歇,走了一天,一抬头,太阳落山了,也到了果园,一估计,时间和里程就都出来了。
三十年前,他三十岁,带了一个五六岁的幼儿,来奔他改嫁至此的生母。
Copyright © 36加盟网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130*1234567
友情提示:投资有风险,咨询请细致,以便成功加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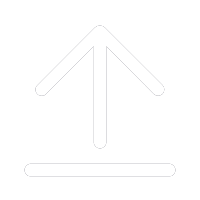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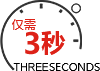
(提交后,企业招商经理马上给您回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