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你好了,我请你吃热干面。”
看到这句写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漫画上的话武汉热干面,顿时让我这个新疆人泪目。它就像说新疆人请你吃拉条子,一听便能找到自己的根。
热干面是武汉人过早的首选小吃。热干面里有长江的味道、黄鹤楼的味道、汉正街的味道、母亲的味道。武汉人对热干面的热爱,像孩子迷恋妈妈的怀抱,与其说是一种日常习惯,一种无可名状的喜欢,不如说是一代代人沉淀在骨子里的文化。
最早知道武汉是从毛泽东的诗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知道“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知道武汉与四川、陕西、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湖北九省相通,是龙兴腹地、九州通衢之地,也是多年以后的事了。但我知道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句字缝里渗出水雾似的旷古悲情。我还知道汉正街,是因读池莉小说。仅此而已,这是我对于武汉的全部认知。我的生活圈子在中国西部新疆,挖祖上三代也找不出一个武汉亲戚,武汉这座城市一直在我的身外,像一个陌生人。
时间的指针滴滴答答走到2005年。
那一年我儿子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几经商量,确定选择湖北荆门长江大学。去学校看望儿子必经武汉。那是我第一次去武汉。游过黄鹤楼、逛过汉正街、汉江路步行街已累得腿脚发软。随便找个小食摊儿坐下,正不知吃啥,一位手拿锅铲,身带围裙的中年男人热情地说:妹妹,来碗热干面吧,来武汉不吃热干面等于没来。
我拿出新疆人的豪爽回应,好,来一碗。
他的街边店挺简单,一个小推车,推车上放着各色调料,旁边烧一大锅滚水,一张小矮桌几把小凳子武汉热干面,我之前已有几个人坐那吃热干面,不知是辣的还是烫的嘴里“呵呵”喘气,让我想起爷爷顺着碗边喝玉米糊糊的样子,那种满足感好像全世界都不存在了,只有眼前这碗饭,用现在最时尚的话说就是吃出了幸福感。我站在摊位前,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个男人抓起一大把不知上面抹着什么油光光的熟面投入笊篱,再把笊篱放进滚水里,没一会儿就把烫热的面倒进碗里,小麻油、榨菜丁、虾皮、酱油、味精、胡椒、葱花、姜米、蒜泥飞速的舀进碗里,动作老练而精准,最后将调好的芝麻酱浇到面条上,搅拌均匀,很体贴地问我,辣椒要多还是少。
我一向胃弱,不敢吃太多辣椒。忙说,嘎嘎的一点。
嘎嘎的一点。他重复着我的话,虽然没听懂但已经意会。我们俩都笑了,他的笑容像武大的樱花般灿烂。
第一次吃热干面的感受太强烈,以至于十五年之后,舌尖仍能轻而易举地捕捉到那种香喷喷、热乎乎的味道。
2013年再去武汉,热干面自不可少,它物美价廉,顿顿吃也不烦,像新疆凉皮子,是百姓的吃食,最接地气。热干面吃得多了,自然吃出微妙的差别。
蔡林记的热干面武汉名声最大,是武汉家喻户晓的老字号。他们家的热干面,爽滑筋道,黄而油润,香而鲜美,“未食而乡情浓浓,诱人食欲;食之则香飘四溢,回味无穷。”蔡林记热干面的黑芝麻酱非常香醇,我爱吃这种黑芝麻酱拌的热干面。除此之外,长子热干面、三毛热干面、蔡明纬热干面在当地也都家喻户晓,且各有各的特色。
在武汉我最喜欢随意转悠,遇到一个小摊儿,看着顺眼,肚子也正好需要,便坐下来吃上一碗热干面,有的香辣,有的咸香,有的面软,有的面硬,对我而言,每一碗热干面都是我与这个城市永不重复的相见,无论怎样,每一次遇见都是此生最好。
离开武汉后再没有吃过热干面。在家尝试着自己做,均以失败告终。食物与一方水土有千丝万缕、根深蒂固的联系,如落在笔端的文字,词节再精准,也很难描摹内心的微波。
2020年,武汉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疫情的发展与变化套牢每一位国人的心,热闹繁华的武汉变得凄苦而清冷。视频里看到一个小店儿仍在卖热干面,在店面和顾客之间搭一块滑板,将做好的热干面装饭盒里,轻轻往前一推,快递小哥在另一端接住,热干面通过这种方式送抵武汉人家,让普普通通的武汉人内心天地辽阔、万物蓬勃,在淡定与焦虑中咬牙挺住,等待疫情结束推门迎春。
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只要热干面还在,武汉的春天必将如期到来。(李佩红)
Copyright © 36加盟网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130*1234567
友情提示:投资有风险,咨询请细致,以便成功加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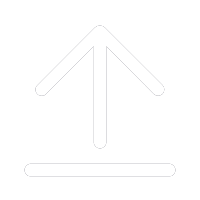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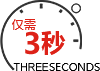
(提交后,企业招商经理马上给您回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