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公会

梁珂:
上个月月末,我从北京出发,去了一趟沈阳,在一家名叫「万顺啤酒屋」的小酒馆呆了一整天。
老沈阳人管这儿叫「穷鬼乐园」。
我第一次听到「穷鬼乐园」,是在作家郑执的一次公开演讲里。他是八零年代生人,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经常来这儿喝酒。在这个东北男孩儿的认知里,「穷鬼乐园」这个地方,驻守的都是整个城市里最失意、最绝望的人。在他看来,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一群被时代遗弃的人,只能在五块钱的廉价啤酒里抱团取暖。
暂且忘掉这些抒情化的文人解读吧。请点开音频,跟我一起在这家小酒馆呆一整天。
⚠️注意:由于整期节目几乎都是在嘈杂的酒馆中录制完成的,建议您戴上耳机,感受更多的声音细节,或参考下面的「字幕」。
-1-
扎啤五元,小菜五元

■ 「穷鬼乐园」的吧台,老板娘英姐(图/梁珂)
客人:扎啤多少钱?
英姐:扎啤五块。
客人:行,给我来一杯。
英姐:来点小菜?热乎的有砂锅、麻辣烫啥的。
客人:我喝点酒就行。
英姐:那就拼个小菜。
客人:这豆腐吗?
英姐:嗯。
客人:行,豆腐、土豆丝儿。
英姐:唉,土豆丝儿。
客人:那个是海带吗?行,给我来点海带。
英姐:一共十块钱。
「支付宝到账,10 元」
英姐:好嘞,坐里面吧,里面暖和。来啦,您要吃点啥啊?
这段对话发生在一家酒馆的吧台前。这位大哥是上午九十点钟来的。他花十块钱点了一扎啤酒、一盘小菜,在靠近吧台的位子上一个人坐到中午才离开。从头到尾,他都没怎么搭理人,一个人发呆、喝酒。
这家酒馆的名字叫「万顺啤酒屋」,位于沈阳市火车北站附近。对于这个地方,老沈阳人有另外一个称呼,他们管这儿叫「穷鬼乐园」。

英姐:
到这边来的都是条件不怎么好的,工薪阶层,或者底层老百姓。
那天老陈问我,为什么起个「穷鬼乐园」的名,我说不是我起的,是大伙起的。可能因为东西便宜,大伙一说到「穷鬼乐园」去,就都知道说的是「万顺啤酒屋」。
这位就是吧台前点菜的大姐。她叫英姐,是「穷鬼乐园」的老板娘。
2019 年 11 月 24 号,我从北京出发去了沈阳,在穷鬼乐园呆了一整天。
这是我第一次来东北。在此之前,我对东北城市的印象主要构建于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郑执、班宇、贾行家和双雪涛的小说,还有一位在哈尔滨读了四年大学的发小。当然,还要加上今年的《野狼 disco》。
这些显然不是东北的全貌,而我也并没有打算在「穷鬼乐园」里窥见东北的全貌。抛开所有文学化的解读,这里不过是一家卖啤酒、麻辣烫和砂锅的老店而已。
英姐:
算下来,我们家开了 32 年。
我二十四五岁时,在一个第三产业的皮箱工厂里做运输工作,经常没有活。
大概 1985、86 年间,结婚都流行赠送皮包,工厂生意还不错,后来老百姓对皮箱不感兴趣了,我们单位也濒临停产,领导说,要么自己干,要么下岗,或者交点钱,停薪留职。
那时刚结婚,我大姑姐正好在大东副食有个铺位。我一想,不如就和我爱人帮着她一起买啤酒,一直干到现在。
我和我爱人分别在 1996、1997 年下岗。1990 年到 1996 年间,是我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上世纪九十年代,像「穷鬼乐园」这样的饭店,在东北很常见,它们的经营者大多是像英姐夫妇这样的下岗职工。
如今,当我们试图观察当代东北时,始终无法回避「下岗潮」这个节点。在各种意义上,它都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对郑执和双雪涛那代人来说,它意味着初中时那笔让父母犯愁的九千块钱借读费;对英姐这一代人来说,它意味着「个体户」这条人生道路的可能性。
于是,在开了三十多年后,这里成为了类似于「时间胶囊」的存在。只要有五块钱的扎啤,五块钱的小菜,这里就是时间以外的乐园。

-2-
生活所迫离开家,行走江湖挣钱花
�� 9:00
「穷鬼乐园」每天上午九点开始营业。八点四十左右,我来到了店里。这里位于两条马路的交叉口,进门以后,是一个狭长的三角形,总共三层楼,都维持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装修原貌。靠近门口的地方,左手边是吧台,右手边是一排窄小的餐桌。
我到的时候,店里的伙计正在吧台忙着准备营业。往里走,靠近窗边的座位上围坐着七八个没有点菜的客人。他们看起来年纪都不小了,大约五六十岁的样子,说话声音很响。
我一问才知道,他们都是装修工人,来附近的北市场找活儿干,一时半会儿等不到活儿,就来店里暖和暖和。
梁珂:你们是在哪儿干活的?
王叔:文官屯有个沈阳职业技术学院,在院里干活。
李叔:在 724(沈阳老地名,旧时军工厂所在地)那儿,工资一直没给咱们。
王叔:欠了好几个月了。
梁珂:欠多少个月了?
王叔:能有两万来块钱吧。
李叔:哪有两万?欠 10 多万了都。
王叔:俺们是给他们教学楼改造维修的,铺瓷砖、抹灰,全部翻新。中央 11 月 1 日开的会议,不允许拖欠农民工工资,违者要关监狱。但他现在就一直推活络车(东北话,指推诿、周旋)不给钱,俺们每天 300 块钱,到现在都没有回复。
王叔:招俺们来的这小子能有四十五六岁,姓周,家是朝阳的。跟我一起干活有个(关系)相当不错的,家也是朝阳的,让我上那去。
李叔:他说 5 天一开支,没开上,6 天、7 天、8 天……我们不干了,他就开了点。但混熟了,就总说「等我几天吧,等我几天吧」,越欠越多,这笔钱还没处要去。辛苦钱不给,你说这不是咱的血汗钱么。都是生活所迫离开家,行走江湖挣钱花,养活孩子和他妈。你说咋整?
王叔:谁不等钱用,家里孩子上学哪不得用钱,咋整?
梁珂:您家小孩多大?
王叔:我家小孩十七八岁,正上学要用钱呢,都这样,他老伴还住院呢。
李叔:住院呢,脑血栓,得瞧病啊。我跟他说了,老伴住院等钱花,白搭,没用。他说那也没招,他也没钱。
这位姓李的大叔告诉我,他是辽宁绥中人,三十多年前,从老家来沈阳打工,一直以来,都是泥瓦匠。
李叔:我 1996 年过来的,家里下放的那点土地不够吃,没办法,我不说嘛,生活所迫离开家。
梁珂:你老家多少人?
李叔:4 口人 10 亩地,吃是够,但不得花么!
梁珂:你们那里来沈阳或者进城的人多吗?
李叔:青年人都出来了,现在就剩老头老太太了。老头不能干,像我,要是在这打不到工,回家弄点地,还得干。我现在 60 多,再干个三五年,干不动了咋办?
聊了一会,这几位大叔打算出去,到门外的路口接着等活儿。
每天上午,他们都会到这来,把自己能干的活儿写在牌子上,拿在手里,或者用绳子挂在身上,等人上前问价。
梁珂:你们一般会等到什么时候?
李叔:到晚上天黑看不着了再回去,至少挣点饭钱,今儿挣 10、20 块的买点菜再回去,不然啥也没有,咋回家啊。没办法,像咱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啊,我估计,得占着几万人。

-3-
歌厅往事
英姐告诉我,这么多年来,路口的地方一直是个约定俗成的劳动力市场。有些人在这里一站就是好几年。
英姐:
他们工作压力也挺大,有下岗的,有农民,但都有点手艺,什么瓦匠、木工、电工啥的,他们都爱在我们门前这个阳光特别足的位置站着,谁家有需要装修的,就到那里去找人干活。
八几年就开始有,那时候人特别多,早晨、中午的时候,一大排人特别壮观。有时候检查的人来了,才会赶他们走。
英姐说,八九十年代,他们门口一天最多能聚集几百个工人,非常热闹。
某些意义上,他们比店里的醉鬼更加落魄,因为连进来喝一杯扎啤的钱他们都舍不得花。
近些年来,市容管制加强,再加上经济凋敝,来这里等活儿的人越来越少,与它一同萧条的还有附近的北市场,以及隔壁的黑舞厅。
英姐:
我们那时候旁边有个舞厅——百乐门舞厅。
有 1000 多(平方)米,挺大,旁边工地的人或者下岗的,都上那儿跳舞去,想找点慰藉。
农村没啥工作的、下岗的有点姿色的女的,也会来这跳舞挣钱,一天百八十块,都以养家为主。
到中午饭点,因为离得近,还便宜,那些跳累了的人都愿意来我们这消遣一下,基本上是满员的状态。
后来这地方要盖成古董行,舞厅也黄(倒闭)了,人就少多了。
原来北市场这个地方特别繁华,一走到街上,行人络绎不绝。现在一看,稀稀疏疏的没几个人,特别萧条。
生意变差后,英姐把三楼租给了一个乒乓球馆,但没过多久,乒乓球馆也倒闭了,英姐就把三楼改成了仓库。但大多数时候,二楼也人丁冷落,只有到饭点儿,才会有一楼坐不下的客人占据那里的大圆桌。

-4-
五年,零九个月
�� 12:00
到了午饭时,店里终于热闹起来,熙熙攘攘的,弥漫着砂锅和麻辣烫的香气。
在酒馆中间,靠近火炉的四人座上,坐了两位看上去六十来岁的大叔。其中靠里面的那个非常显眼,他穿着一身带毛领的藏青色大衣,戴副眼镜,皮鞋一尘不染,显得颇为体面。我坐到他右手边的空位,和他闲聊了几句。他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三十年前,就常来喝酒。
这位衣着体面的大叔姓赵,坐在对面的,是他的老朋友,姓罗。
罗叔:他这屋啊,什么人都不嫌弃,别惹事、别闹就行。冬天没地方去,在外头也冷,在这花 5 块、8 块、10 块,可以坐半天,不会撵你。我跟你说啤酒屋,现在咱都 60 多岁了,咱是 20 多岁就在这一起喝酒的。真的,一点不撒谎。
赵叔:从它开铁棚的时候,就在这喝。那时候是大罐啤酒,八几年,两块钱一杯。
罗叔:那时候下班了就在这喝,和朋友几个。
赵叔:这地方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穷人也来,富人也来,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赵叔和罗叔是很多年的朋友。赵叔告诉我,这家酒馆是他和老朋友最常聚会的地方,但也是他的伤心地。六年前的一天,他在「穷鬼乐园」喝酒时,碰到了一件大事。
赵叔:我搁这屋吃饭,也是这个桌儿,我没跟人打,判我 5 年 9 个月,去年刚回来,2012 年的事,这老板都知道。
罗叔:这事儿是有,他有点窝囊,冤枉。
赵叔:不是窝囊,就是冤枉。
罗叔:别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赵叔:简单地(介绍下),搁这桌吃饭,我当时给朋友买了条烟,他想把烟扯开,就是“被害人”。
罗叔:他(“被害人”)想抽,想拿走。
赵叔:我朋友就说“这是我赵哥给我买的烟,你别动”,就没动。当时他拿出一盒玉溪来,显摆一下,说我的烟不合格,他都有玉溪。但咱也没吱声,你有玉溪,你就是有中华咱都不挨着,对吧?但他说我是外地氓流子(东北话,指小混混、无赖),三说两说瞧不起我,我说我外地氓流子也不差你事啊。
罗叔:我差你啥啊,我就打你咋的。
赵叔:没有,那话没有啊,没说那话。
罗叔:不是我说的,我这开玩笑。
赵叔:当时他说他眼睛瞎了,上派出所,就北市派出所。去了三次,也没拘我。证据不足,抓不了我。后来人家找人给我整进去的,又给我办了取保,待了 12 天,我没搭理,因为我满身是理,搭理他干啥,最后反而给我送进去了。
姑娘,我跟你说句话,这眼睛如果是我打瞎的,判我 5 年 9 个月,我值,不管怎么,人家好眼睛给打瞎了,值个儿。但我没打,我冤枉,判决书上都没证据。只有一个监控,这么写的,「因监控录像部分被遮挡,无法证实被打的部位」。
梁珂:监控拍到什么了?
赵叔:拍到我踢他后屁股两脚,他眼睛瞎了。我踢的后屁股与眼睛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有罪,我认了,再给我整进去,我也认,对不对?
罗叔:(他)老妈,因为他进去,气得上火了,没了。真的,这我知道的。
赵叔:他知道。我姑娘现在不搭理我,说你看,爸爸你这么大岁数跟人家打仗,就不跟我说话,老母亲没了,媳妇离婚了,老大挫折了,是不是,姑娘?
梁珂:您去年出来的?
赵叔:去年 11 月份出来的,今年 1 周年了。
赵叔:我刚回来,接受不了这社会的环境,物价高。原先我理个发 5 块钱,我回来 15 块,接受不了。
赵叔:这地方没变,还这样,5 年也没变。房子还是这个房子,生活标准还这样,没变。
赵叔:我第一次回来啊,哎?小罗?是去年 12 月份吧?我给你打电话,是不?也是这桌,这我朋友,我始终不能忘他,他搁这屋,请我吃顿饭,给我接风。
罗叔:老伙伴啦。
赵叔:喝点小酒,唠唠嗑。
罗叔:跟菜没关系。
赵叔:在监狱待着挺不容易,我回来那个时候,相当地难呐,我弟弟给我 500 块钱,算维持生活了。
罗叔:行了,别说了,现在不挺好的嘛,工作找着了……
赵叔:我实话实说,我兄弟给我 500,「哥,你得活着!得生活,往好处发展!」
罗叔:没有多,有少对不?咱们说,我给你拿 1 万,没有;拿 500,咱是朋友情,我就这么多了。他出了这个事,不爱在这地方喝酒,他的伤心地!妹妹啊,这里老了故事了,伤心的、高兴的,都有。
聊了半天,桌上的几扎啤酒都喝光了。罗叔喊来伙计,又加了六瓶啤酒。加上原先点的一份砂锅,几盘小菜,和两三扎生啤,他们一共花了 51 块钱。
梁珂:您哪儿的人啊?
赵叔:我是葫芦岛人,兴城,锦西。
梁珂:您什么时候来的沈阳?
赵叔:我头三十多年前就来了。
赵叔: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就是做点生意,搁南二市场,干调,花椒、大料、葱、姜、蒜。
那阵还行,现在不好做。现在床费(铺位租金)也高,物价也高,只能维持糊口。
赵叔:生意不好就不干了,打工,出点力,还旱涝保收。
罗叔:在三好街百脑汇,他是保洁,我保安。
赵叔:我 60 了,现在打工,找连锁店,肯定不用你;找私营的,像这屋,超 60 还可以用你。我外孙女上学,学费要得高,所以说 60 岁还得靠自己打拼,给孩子减少点负担。她(女儿)不搭理,我也考虑孩子,也有因素,不容易。
梁珂:你现在回想起来,你家日子过得最好的是什么时候?
赵叔:我姑娘 1980 年生的,81、82 年是我家最好的时候,因为我农村,那时候分产到户,我自己搞单干。我养车,那时候我生活是相当不错了。一般农村老百姓都喝散白酒,我得喝瓶白酒。
罗叔:那时候多牛,你还是我大哥!别吹了!现在我得请他,受老冤了是不?
赵叔:你看!说出来了,受老冤了!俺们多少年了都,你说咱都多少年了?三十多年了!别话不多说了,再说多了我眼泪都下来了。
赵叔:我来,我来!
罗叔:别扯了,你给我呆着吧。
赵叔:完事了,不喝了。
罗叔:完事了,下午还得回家睡觉,看篮球,辽宁跟北京。

-5-
酒浑子
�� 14:00
下午两三点,赵叔和罗叔离开了啤酒屋。店里的伙计,王师傅在一旁拖地板。我向他打听了他一下,想了解一下赵叔的案子,但他也记得不太真切。
王师傅已经在这家酒馆工作十八年了,在他的记忆里,这里发生过的类似事件实在太多,酒精不止是麻醉剂,同时也是愤怒和暴力的催化剂。
王师傅:
我以前接触的人和他们这些酒懵子(酒鬼)不一样,到这来头一天,看这些人说话骂骂咧咧的,就打退堂鼓。后来一合计,还是先照量照量(东北话,表示尝试),适者生存,后来就习惯了,现在没有他们闹了,还觉得没意思。
王师傅说,他的脾气并不好,但来店里干了这么多年,见识了那么多暴躁的酒鬼,也逐渐学会了收敛。他是沈阳本地人,以前是一名退伍军人。
王师傅:
我转业回来,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回来以后不给安排工作,就去卖水产,生意还行,那几年钱好挣。我做买卖的时候,冷库一开,大货车直接怼到库门口往车上装,一天挣万八儿的不费劲。
那时候工人也好过,奖金都吃不了地吃,那时候钱多,现在老百姓兜里没有钱,那时候活鱼、活虾,还有虾爬子,一块钱买的,两块钱卖,往门口一摆啤酒屋,一会就没,老百姓呼呼的(表示蜂拥而至),后来一年不如一年。
生意不好做了,我也就退了,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半夜12点就得去上货,也不容易。
原来,我儿子给我开车进货,我老伴和儿媳妇帮忙占床子(看管铺位)。现在不干了,我儿子、儿媳妇跑运输,我老伴在家带孙子,我出来挣点零花钱,我当兵还有劳保,这基本生活能维持。
�� 16:00
正和王叔聊着,英姐也来了店里。英姐一般会在上午十一点左右来店里招呼客人,中午一两点钟回家休息,四五点钟再回到店里,一直呆到半夜两点打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英姐说,最近这些年,沈阳的治安已经好了很多,但酒馆毕竟是是非之地,打架斗殴时有发生。
英姐:
因为本身我是女的,有的男同志喝酒闹事了,我说他们,还真听。有时候,我也挺理解那种感觉。
有一次,一个顾客,好像是跟他媳妇俩打仗。一进来就说“给我来两杯”,还没等喝呢,就开始叮了咣啷地砸桌子。
我说,「小伙你有什么事吗?」
「我跟我媳妇要离婚!」
我说,「咱是个爷们,有什么事可以跟媳妇心平气和地唠,不能砸桌子!」
「行!老板娘我听你的!」
这功夫,媳妇也打电话了,「你赶紧回来,咱俩好好唠唠。」
回去之后,俩人没说好又打起来了。
他就回到店里,给我的店里砸得乒了乓啷(指乱七八糟)的。
他觉得好像把心里的气都撒出来了。
我说,「小伙,你为什么不砸你自己家呢?」
他说,「姐,没事,你放心,你这瓶子啥的我都给你赔了。我就觉得在万顺这把这气撒出去了,一切就顺利了。」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虽然一天挺累,但没事唠唠嗑挺好。
有些老顾客,有时候几天不来,我都想他们,一来,我就说「你咋才来,我都想你了!」
他们说我玩虚的,我真不是,我就是比较怀旧的人。

■ 「穷鬼乐园」门口的鱼缸(图/梁珂)
-6-
「哪能一辈子给人打工啊」
�� 19:00
英姐能认出他的每位老顾客。在吧台边,每次有老顾客来点菜,她就会给我介绍,这是谁,是干什么的,一般什么时候来,喜欢坐哪儿,喜欢点什么菜。
大约六七点,店里来了个年轻客人,看上去不太爱说话,英姐说,他叫小李,原先在附近的一家正骨店打工,经常来,喜欢吃面。点完菜后,小李就坐到了角落里,一声不响地看店里的电视。
梁珂:老板娘说您现在附近上班呢。
小李:我现在不在这,我自己开店了。
梁珂:什么店啊?
小李:正骨店,治疗的,骨科诊所。就治治颈椎病、腰托什么的。
小李听说我是打北京来的,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很多年前,他也当过北漂。
小李:北京我也呆过,海淀、丰台、昌平、朝阳区,我都待过。
那时候还没学这技术呢,搁北京干过物流、后厨,卖过房子,都是挺多年前了。
其实我觉得人在哪生活都无所谓,哪个地方适合你发展,在哪个地方有前途,就 OK 了,在哪都一样!
我家不是沈阳的,我家黑龙江的,学这个技术也是偶然间的。
跟我师父学的,医院没有,都是家里祖上传下来的,也不是谁都收的。
关系不错的人介绍的,正好还比较合适,我有劲,身体素质好,自己还有点悟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还得能耐得住寂寞。
这就成为我的终身职业了。我不会再选别的职业了。
还是挺喜欢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现在我已经自己开店了,也属于一个事业了;
第三,年龄到了,不允许再换职业了,即使再找到别的事业了,也不见得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
这属于治疗,救人治病的,有风险、有责任,治好了有成就感。
自己创业是早晚的事,谁也不可能给人打一辈子工。
现在才两个半月,说能不能开成还为时太早,但目前来讲效果还不错,我有固定的会员 20 个,长期消费的,长期来给你送钱的。
你像我现在就今天出来放松一下,我一周星期一到星期六 6 天时间,天天在店里待着,来人就干活,没有人就呆着。
再累也能坚持,关键收入自己赚的,多少钱都揣自己腰包里了,再累也值个儿!咱说挣不到大钱,但比打工强多了,强很多倍。

小李吃完饭就离开了,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吃了一份老板娘刚煮的水饺。
-7-
这里不是「深夜食堂」
�� 21:00
晚上,「穷鬼乐园」又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靠近门的位子坐了一位流浪汉,英姐告诉我,他是个无家可归的聋哑人,每天到这个点来店里,吃点残羹剩饭,在窗边呆坐一整晚。
靠近吧台的位子坐了十来个醉醺醺的中年人,一边喝扎啤一边用含混的口音高谈阔论。
靠近火炉的位子,两个戴棒球帽的年轻人喝着啤酒,啃着鸡架,聊了一晚上项目欠款。
接近午夜,三五成群的酒鬼才相互搀扶着离开,店里只剩下几个独自喝闷酒的男人,还有刚下班的外卖小哥。偶尔会有住在附近的年轻人上门,点份夜宵,匆忙打包带走。

快打烊时,店里来了两个年轻男人,胖的点了份面食,要打包。瘦的那个什么都没点,面无表情的站在一边,他没化妆,但眉毛显然有修过的痕迹,穿着时髦的皮草外套。我随口一问,发现他竟是半个同行,他叫奚祈君,曾在上海一家时尚杂志当编辑。
�� 24:00
小奚:
我是交通大学毕业的,比较喜欢时装搭配,毕业前一年的实习期,开始写一些时尚搭配的文字,之后这些书都会给员工看,慢慢也就做了培训教师。
我做的是 LV 服装陈列,摆摆衣服、给衣服做做造型,帮店铺设计灯光和舞美,知道衣服是什么材质,商家这一季的服装主题,设计的走线和版型以及设计师的灵感来源。
慢慢开始做淘宝模特,我感觉这个行业赚钱,10 套衣服 8000 块,如果一个月多接几单,就暴富了!
但是时间一长,行业饱和了,现在长得好看的人实在太不缺,特别是南方人。经朋友和领导介绍,我就去做了杂志,一直到现在。
后来因为上海的房价太高,没钱买房,就回来了。
前年我爷爷病逝,今年年初我姥姥也走了,家里给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想让我考个公务员,守着四方格工作,能过活就行。他们对我的期望就是这样。
回来后,感觉跟东北格格不入,因为我经历的好像都是东北未来半个世纪的事情。
现在已经呆了半年,落差实在是太大了,真心接受不了,一直很不开心。
我吃南方菜习惯了,东北菜太咸了,我受不了。
回沈阳后,奚祈君依然在集团所属的杂志工作,负责东北的一些业务,尽管他依然在自己热爱的时尚产业里,但他已经看不到自己职业发展的未来了。

■ 时间接近凌晨一点,「穷鬼乐园」要打烊了(图/梁珂)
小奚:
东北这边没活,就是处理一些杂碎的事情。别人没弄好的,我们拿来修改。
基本上外拍、采访都没有,我们就负责处理烂摊子,闲职,适合养老。
我是主编,招聘会跟着一起复试。
有很多员工因为加班不想干,距离远不想干,工作时间长不想干,总出差不想干。
我在南方没有遇到过,从来没有,我们有时候加班,连着三四天都回不成家,很正常。
我们上海公司几个小女孩,实习生,家住在上海跟江苏的边界,早上高铁倒地铁,一个半钟头能到公司,天天劲儿劲儿的上班,一个月 8000 多点,人家从来没有感觉到困难,不像东北人,东北的惰性就导致它发展慢。
我现在都不敢跟以前的同事、同学谈工资,没法说出口,随便一个张嘴就年薪百万,最次也八九十万,我都不敢谈。
有一回我之前的同事问我,在东北怎么样?薪资待遇怎么样?过得好不好?
我说挺好的,没法说。
在我们坐下来聊天的时候,和奚祈君一起来的朋友默默坐在远处的位子上,吃完了他准备打包带走的食物。然后,他们两手空空地离开「穷鬼乐园」,消失在了空旷的夜色里。
而英姐她们,也准备打烊了。
——————
配图来自
大众点评网友照片
Staff
讲述者 | 英姐 王叔 李叔 罗叔 赵叔 王师傅 小李 小奚
主播 | @寇爱哲
制作人 | 梁珂
声音设计 | @故事FM 彭寒
文字 联络 | 吴梦翼
运营 | 翌辰
Copyright © 36加盟网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130*1234567
友情提示:投资有风险,咨询请细致,以便成功加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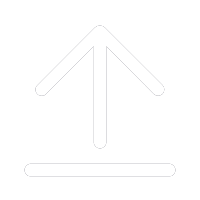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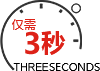
(提交后,企业招商经理马上给您回拨)
